一、佛陀时代的佛教乐艺弘法与中国梵呗弘扬
佛教音乐,远溯于印度的“吠陀”。吠陀为婆罗门教基本文献之神圣知识宝库,用于祭祀仪式招请、赞咏与歌咏有密切关联之宗教文献。分为:一梨俱吠陀:招请诸神降临祭场并赞唱诸神之威德。二、祭祀时配合一定旋律而歌唱的沙摩吠陀。三、唱诵祭词,担当祭仪、斋供等祭式实务之夜柔吠陀。四、加上于祭仪之始,具足息灾、增益本领,并总兼全盘祭式者,属总监祭式之内容称阿闼婆吠陀,即成四吠陀。内容大约分赞诵与实际仪式作法两大部分,前者多用以供养或歌颂火焰、太阳、大气、虚空、风等神格化之自然现象,内容系有关祈求健康、财富、长寿、家畜、子孙、胜利、灭罪等之祈祷文。以此类赞诵多属对神德之赞叹,且多由感念沐浴神之恩宠而自然涌现的祈愿之词,故又称赞歌(梵 mantra)。作法方面则揭示祭典典例、供牺之由来、赞歌之用法等有关仪式作法之解说。
古吠陀时代盛行歌咏偈颂,佛陀沿用此法作为弘扬佛法的方便,用此法赞咏、歌颂佛德,称为“声呗”。
《十诵律》中,佛陀赞许跋提比丘:“听汝作声呗,呗有五种利益:一、身体不疲;二、不忘所忆;三、心不疲劳;四、声音不坏;五、言语易解。”由此可见,音乐可用来表达人类内心的情感。一首神圣的乐曲,或虔诚的佛赞,可以把人的心灵升华到圣洁的境界,所以就宗教弘法而言,音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
《大智度论》也云:“菩萨欲净佛土故,求好音声;欲使国土中众生闻好音声,其心柔软;心柔软故,受化易,是故以音声因缘供养佛。”音乐不但使人心柔软,容易信解佛陀的教法,并且令身心柔软,受持不忘。
在佛经常以歌咏赞诵佛德之内容,及天人以歌舞乐咏赞叹庄严法会描述。例如《阿弥陀经》中云:“彼佛国土,常作天乐。…是诸众鸟,昼夜六时,出和雅音。”“彼佛国土,微风吹动,诸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,譬如百千种乐同时俱作,闻是音者,自然皆生念佛、念法、念僧之心。”由此可知在极乐世界里的梵音都在传达佛陀的教法,令人产生欣喜好乐三宝的善法欲。
佛陀在世时,佛教中有名的马鸣菩萨正是以音乐弘法的最佳表率。西元110年左右,马鸣生于中印度,本学婆罗门外道,长于音乐诗歌声誉卓著,后为胁尊者所论破而归依佛教。马鸣曾编导“赖吒和罗”佛教戏曲,竟令观众深感无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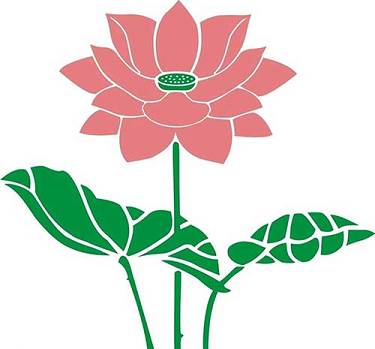
佛曲在天竺时极盛,据梁慧皎《高僧传》记载鸠摩罗什语:“天竺国俗,甚重文制,其宫商体韵,以人弦为善……见佛之仪,以歌赞为贵”。佛教传人中国后,为僧伽之礼佛仪式所需。因此既有礼佛之仪,则有赞呗之需。但当时在华传授梵呗的僧人,大都是西域或天竺人。
三国时.中国的佛教徒开始注意到“梵音重复,汉语单奇,若用梵音以咏汉语,则声繁而偈促;若用汉曲以咏梵文,则韵短而辞长”的矛盾并开始创作中国化的佛曲。曹植是“改梵为秦”的中国化佛曲--梵呗之音创始者。相传陈思王曹植擅于诗歌、乐曲,一日于山东省的鱼山,听闻空中有梵音歌赞,其声清雅,委婉动人,深有体会,便摹拟音节,并依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的内容编撰唱词填入曲调,于是创制中国所独有的梵呗法。他所创作的“鱼山梵呗”,成为我国佛教梵呗之始,为中国的梵乐奠下基础。
齐梁时,佛教兴盛,“南朝四百八十寺,多少楼台烟雨中”,永明七年(西元489),竟陵文宣王萧子良“集京师善声沙门”于一处,专门创作研讨佛教音乐。参加者有龙光、普知、新安、道兴、多宝、慧忍、天宝、超胜、僧辩等。这次集会,对以"哀婉”为主要特征的南方梵呗风格的确立,起了重要的作用。
梁武帝萧衍,笃信佛教,且“素精乐律”,他曾利用裁定梁朝雅乐的机会亲制“《善哉》、《大乐》、《大欢》、《天道》、《仙道》、《神王》、《龙王》、《灭过恶》、《除爱水》、《断苦轮》等十篇,名为正乐,皆述佛法”。还开创童声演唱佛曲,如“法乐童子技”、“童子倚歌梵呗”等。除此之外,他又创设“无遮大会”、“盂兰盆会”、“梁皇宝忏”等佛教轨仪,将梵呗唱颂应用于法会忏仪中,为佛教音乐提供了新的形式范例。梁武帝在佛教音乐的贡献,佛曲的清乐化,是佛教音乐开始与中国传统音乐融合的展现。
还有敦煌说唱弘讲,此宣扬的方式,使佛教在当时极受欢迎。
然而在宫廷,来自西域佛国的音乐,成了当时上层人士的“流行音乐”。如唐懿宗时,佛诞之月,“于宫中结彩为寺”,宫廷音乐家李可及“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”,“作菩萨蛮舞,如佛诞生”,整个宫廷,似乎都变成了节日的寺庙。
在民间,佛教音乐也成了社会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。姚合“仍闻开讲日,湖上少渔船”,“远近持斋来谛听,酒坊鱼市尽无人”,以及韩愈〈华山女〉诗“街东街西讲佛经,撞钟吹螺闹宫廷”的诗句,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佛教俗讲僧们对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影响。他们不但在岁时节日举行俗讲,并由寺院发起组织社邑,定期斋会念经,且有化俗法师不殚劳苦,游行村落,以最通俗的形式劝善化恶。
因此,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的认识,认为佛教音乐的目的是“宣唱法理,开导众心” (慧皎《高僧传·唱导篇》),是“集众行香,取其静摄专仰也” (道宣《续高僧传·杂科声律)决定了佛教的音乐美学观念:以静、远、肃穆、平和为高,而反对“淫音婉娈,娇弄颇繁”。
但随著时代的演变,固定化的佛教音乐,无法满足现代人的心灵需求。自民国以来,大众对佛教音乐已逐渐疏远,甚至沦落只剩经忏佛事的佛教音乐。有鉴于此,西元一九三○年,太虚大师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与弘一大师共同写了一首词曲优美的“三宝歌”,他们呼吁大众要发扬佛教音乐。弘一大师是一位音乐家,其生前所作的歌曲,经由后人选出了十首具佛教意味和园林思想的歌曲,印行出版成《清凉歌集》。但一般社会大众对佛教音乐仍是陌生,并未能广泛推行于人间。
星云大师认为:现代化的佛教音乐著重契入生活,净化人心,以求情感佛法化,达到教化的功能。今日资讯设备、传播媒体日益进步,我们必须充份运用现代化的科技,以有效率的资讯来表现佛教音乐,例如运用电视、电台等传播媒体以音乐突破人文背景、社会习俗、各国语言的种种障碍;甚至像古典乐器、雷射唱片、电子琴、钢琴及各种交响乐器的运用,以配合社会大众的喜爱及需求。
所以有了,一九五七年,我带领宜兰念佛会青年歌咏队灌制佛教唱片,总共录了六张十英寸的唱片,收录二十余首佛曲。这六张唱片是佛教史上的空前作品,也是划时代的创举,当时虽然引起佛教界一些人不以为然,但我并不气馁,继续在一九七九年、一九九○年、一九九二年、一九九五年,假台北国父纪念馆、国家音乐厅等举办多场梵音乐舞及音乐弘法大会,第一次将佛教的梵呗音乐带入国家音乐殿堂。其中,一九九五年是应“台北市政府”之邀,以“礼赞十方佛--梵音乐舞”参与传统艺术季的演出,将传统的梵呗音乐与现代的佛教圣歌,配合国乐、西乐、舞蹈共同演出,此次史无前例的创举,已能受到社会大众的肯定,与佛教界高度的认同。
二○○三年为纪念星云大师创作佛教音乐五十周年,也为了让佛教音乐更普及化、大众化,佛光山宗委会及佛光山文教基金会特别主办“人间音缘—星云大师佛教歌曲音乐发表会”征曲活动。更将佛教歌曲推广至全球五大洲的机缘。